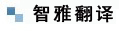| 林文月:翻译时不要统统变成中国味 |
林文月,1933年出生于上海日本租界,启蒙教育为日文,至小学六年级返归台湾,始接受中文教育。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同年留校任教,至1993年退休。曾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史丹福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担任客座教授。曾二度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散文类)、翻译成就奖等。 南都讯 记者赵大伟上周六,台湾建筑师郭思敏来方所举行“形,和他的游戏”雕塑展,跟她一起到来的,还有她的母亲林文月。周日下午,79岁的林文月站在讲台上,轻声细语,把她翻译《源氏物语》的过程对读者娓娓道来。 本月25日,林文月受北京大学之邀请,将举行名为“拟古从《江湾路忆往》到《我所不认识的刘呐鸥》”的讲座,在方所的讲座结束之后,林文月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翻译需灵敏,需翻译出语调 南都:你在《源氏物语》序言中说,翻译避免陷入现代化,尤忌外来语法羼入? 林文月: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不知不觉就受到外来语影响,可是在翻译1000年以前的文学时,我不可以用现在这种的调子来翻译。这是一个原则。我们现在很多文法受到欧美语影响,不知不觉以为它是我们很老的一种语言。 南都:讲座中你说,翻译也要特别注意日文音调的问题? 林文月:我觉得翻译的人比一般的读者更灵敏,你不是只把它的内容看懂了就行。人生的主题也不过是生老病死、悲欢哀乐,可是你怎么把它讲出来,你用什么样的语调讲出来很重要。比如我翻译《源氏物语》,后来我也翻译《枕草子》。这两个女性的个性不一样,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源氏物语》很委婉、缠绵、华丽。可清少纳言比较率直,比较刚强,所以我不能够把这两个作者翻译成同样的味道。其实我也比较不容易摆脱我自己,可是我尽量试着去把我感受到的这个人的表情或者声音表现出来。 南都:在整部作品的翻译风格上,如何对比你与周作人翻译上的差别? 林文月:我并不想把《源氏物语》变成21世纪的,我想呈现它的11世纪。其实当时(翻译前)我没有看到周作人翻译的《枕草子》,没有看到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也是不幸,也是幸,不然我根本不敢提笔了。所以也好,后来我才看到,比较比较看,是有些不同。我觉得可能中国人,比较老派的,读丰子恺先生(的译本)会觉得比较舒服,因为很像我们看的宋人话本那样的。 南都:你会不会发现他们的局限性? 林文月:老实说我觉得丰先生太偏袒中国人。或者他本来想写给中国人看的。我也是想要介绍给中国人,可是我希望他不要以为那个时代就是中国的话本的时候,它没有“话说什么”,没有这样的句子。在中学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外国小说的翻译,我觉得俄国的书有俄国味道,法国有法国味道的。这样子我觉得才是我在看的,不要通通变成中国的味道。 谈文学,回家扫地、烧饭 南都:你的好友林海音、齐邦媛如今 南都专访 也为内地读者熟知,如何看待女性视角? 林文月:其实我没有做过男性,我不知道男性是什么观点。我觉得我自己在讲台上,在书房里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我是什么性别。也有人说我翻译《源氏物语》比较占便宜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丰子恺不是,这是读者的判断,我自己不知道。可能有吧,有的话其实也不是有意识的。 我跟林海音、齐邦媛的确是好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叫殷张兰熙,殷之浩的太太。我们四个人常常会在一起,隔一段时间就聚聚,我们的话题不是很女性的那种,我们讲的都是文学翻译的种种问题。我觉得我们喜欢关心文学周遭的事情,可是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标新立异女性之上,这个没有,我们回家还是扫地、烧饭。 南都:你会看村上春树一些流行的作家作品吗? 林文月:老实说我不大看。当然偶尔看,会。但是我宁可看它的原文。 南都:前段时间对林少华翻译村上春树有批评,有人说他个人创作的成分太多。 林文月:翻译要挑毛病是很容易的,日本人自己的学界就有不同的意见,我有的时候也会碰到,我的方法就是把我比较同意的翻出来,可是我会在注解上说,这个又有一说。 丰子恺也没有像林少华这样做。丰子恺只是表现的方式上,不用“从前”,常常说“话说”。我不要用宋人用的一种词。不过我很佩服周作人、丰子恺,在中国还没有走出来(的时代),他们居然做这么大的工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