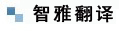| 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多维考量 |
一、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三重诱因
(一)政治维度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自1840年,泱泱“天朝上国”沦为“双半社会”,“救亡图存”成为一个急迫而现实的最强音。各种社会力量纷纷探寻救国救民之道,在这种“师夷长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理论一道,借助翻译纳入国人视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被中国人译介、认可、接受、宣讲并应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2]“恃风雷”的黑暗晚清,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一次又一次地呐喊,一次又一次地战斗!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地向西方学习。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主要有日本、西欧和俄国三条路径。从翻译目标指向看,民国前马克思主义翻译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强烈的目的性和急切的实践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3]
(二)经济维度
随着清末战争的一再失败,战争耗费和巨额赔款导致白银源源外流,太平天国、义和团、资产阶级革命等又沉重铲削了国家的经济基石。特别是被寄厚望的洋务运动破产和甲午战争的惨败更使人们纠结于中国采用何种经济体制,发展何种经济模式,以及如何认知严峻的经济现状。而西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成熟的近代化经济运行机制,教人艳羡。比如,快速崛起的日本当时就成为国人效仿的样板,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国人对欧、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诸多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探索和翻译。可见译介的旨归是寻觅这些国家繁荣强盛背后的思想、政治、经济等的深层动因。
(三)文化维度
清朝末年,“华夏中心论”轰然坍塌、“蛮夷戎狄”的坚船利炮和“蕞尔小夷”的甲午大胜,使先进知识分子忧心如焚而“中夜四五叹”(李白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世界、重新考量东瀛,崇拜欧美的心理便一天高似一天。屡战屡败严重挫伤了中国人自信心和自尊心,各个阶层的士大夫都秉持自己的目的,汲取自己所需的文化养料,调适自己的心理结构,编织自己的理想。一些爱国志士为了拯救中华,也希望从西方借鉴一些救国、强国之道。因此,当时出现了大量翻译西方文献的翻译高潮,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亦囊括其中。
二、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译学向度
(一)文本选择
民国前翻译深源于当时社会的内在诉求,是特定国情的时代选择和文化必然,这一点从翻译的文本选择清楚体现。民国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著作的传播为载体,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主,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一系列社会主义著作等。此类文本深具意识形态性、政治性、当下性、实践性、社会性等表征,基本是为资产阶级提供参照和借鉴。从翻译领域看,文本主要涉及唯物论、进化论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帝国主义学说等。
(二)易读便捷
维新派强调译书的可读性与便捷性,他们认为译作必须易为世人所接受才能彰显其价值。他们指出,译者“倘能更以极明浅之文、恒习之字,……老妪都解……其收效不益广且远乎?”[4]在中国翻译史上,维新派首次提出关于翻译的标准、译书的选择、译作的可读性等全新问题,引发了学界深入思考与广泛讨论,这在当时无疑是耳目一新的。梁启超对翻译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亲自翻译,而在于他创办译书院,从一定的理论高度上引领翻译的潮流。依照梁启超的标准,首先必须谨慎选择所译之书;其次应该制定翻译的规则,特别是统一译名;再者就是关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他倡导以翻译传播文化,并且倡导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将外文书籍译出。维新派于中国翻译史上首次亮出了系统的较为成熟的翻译理论,而且一度跃升为中国近代翻译史的理论主体(自1840年到1919年)。众所周知,维新派的主要论述和重要思想刚好展示于我国内忧外患及血雨腥风的时代。值此紧要关头,他们的翻译当然地和救亡图存深度契合。为了救国这个目标指向,维新派志士纷纷转向欧美去求索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维新派志士拒斥了洋务派人员仅属意翻译自然科学书籍之狭隘性及片面性,将着力目光聚焦至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出版和宣讲。他们强烈呼吁并身体力行译介、出版、发行欧美(含日本)法律、宪法、哲学、历史、政治、伦理、经济、农业、交通、矿业等领域的书籍、文章及教科书,同时深度体认到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并且,他们发现并呼吁翻译日文书籍比欧美书籍便利……所有这些主张都突破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洋务派所极力鼓吹)的藩篱边界。
而且,维新派第一次于中国翻译史上亮出了翻译的各项标则。比如,马建忠于1894年就阐述了“善译”的原则,严复于1898年析论的翻译基准“信”、“达”、“雅”时至当下仍有众多学者在研究和反思。不过,因为本论文主要以翻译史为目标指向,所以对“信”、“达”、“雅”等翻译的各项标则不进行深广研究。本人经过研究发现,对于民众对译书的可接受性维新派极为关注并竭力实现,他们声明,译者之使命就是让更多民众于更短的时间内吸纳更多的西方知识。毋庸置疑,可接受性决定着译作普及的深度和广度。维新派的理念强力助推了20世纪初翻译成果的普及和传播。另外,维新派亦非常重视对各级各类翻译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因此,维新派的翻译实践较前世译者,不管是于译书的选择还是在其译作的民众影响和社会功能上,无不具有进步性和震撼性,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为严复、林纾及梁启超。三人主要着眼于翻译人文社科书籍及国外期刊、报纸等出版物上的文章。众所周知,由梁启超及严复分别主笔的《时务报》与《国闻报》于当时乃南北舆论界之首。为了研读、借鉴欧美历史,他们又翻译并著文论述了多国的历史概况。作为维新派佼佼者,严复翻译了18世纪欧美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哲学及法学的各种代表论著。而且,维新派很早就体认到了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并躬身实践,像林纾就于20多年里独自翻译出10个国家97位作家的183部著作的惊人成就。
(三)变译为主
从译学上讲,主要有两种样态:一为变译(摘译、缩译、译述等);二为全译,而且变译先于全译。民国前马克思主义翻译都是节译、摘译,甚至只评介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而无真正现代意义的全译。从现代汉语看,这些翻译可能并不精当,不“信”,不对等,而从翻译标准看,这些翻译具古文特色,有明显的“归化”(“汉化”、“接近读者”)倾向。从翻译方式看,很多来自日译文或日语译评,常由中国留日学生翻译而成,当然也有直接从欧洲(比如法国)译来的,有的还是由外籍传教士翻译,然后国人润色。
三、晚清翻译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态度
(一)维新派态度
维新派激烈抨击洋务派的翻译观,亮出了他们的翻译出版思想,即必须将翻译出版的选题内容偏于西方的历史与政治、法律制度等,目的是论证变法维新是救国图强的唯一出路。梁启超说:“夫政法者,立国之本。日本变法,则先变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异也,故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而译之。”[5]后来他又强调:“今日欲举百废,就庶政,以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为第一义。”[6]可见,维新派对马克思主义翻译旨于“牖新知”,不是要实际实施。康有为将工人对抗资本家看成是贫富之争,将共产主义翻译成“均产之说”。梁启超则坚决主张,社会主义是偏激,在如今中国断不可实施,而且就是在欧美也不可实施,“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 [7]。梁启超等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是很表层的,甚至根本错误。而且,维新派力图将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糅合,比如康梁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无法实现的极乐世界。梁启超1903年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妄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为“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所以,后来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极力诋毁、对抗社会主义。概言之,维新派只是把马恩著作当作一种学派来介绍,并非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倾向是防范和排斥的。该情形的真正社会历史诱因,乃在于此刻我国客观政治经济生态没有科学认知与广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之基;理论来源是他们基于狭隘的阶级立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有选择地翻译和剥离而产生“误译”、“误读”和“曲解”。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态度
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或赞赏社会主义,却又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们提出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8],只能是主观想像的,列宁曾称其为民粹主义。有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则接受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国家、阶级和私有制,其手段则是“敛也,铳也,爆裂弹也”(大我:《新社会之理论》,载《浙江潮》第8号)。正如朱执信所讲,资产阶级革命派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因,是“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9] 。他们拒斥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埋葬资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孙中山则将社会主义简单归结成“曰社会生计而已矣”[10]。由于政治目标之故,致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将马克思主义误读、曲解和非难,比如同盟会员的翻译,主要服务于他们的政治主张,仍落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窠臼,甚至扭曲马克思主义。此外,以江亢虎为骨干的中国社会党,遵循所谓的“世界社会主义目的和国家社会主义手段”的社会主义学说,于该党的期刊《新世界》里,阐述了马儿克(马克思)的思想,并发表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著)的一多半译文(以《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作标题)。无政府主义者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论证无政府主义较马克思主义更科学。他们横加指责“马氏学说之弊”,强调“故由社会主义扩张之,必达无政府主义这一境”[11] 。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52.
[3]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著.毛泽东生活档案:上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89.
[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47.
[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册[M].上海:中华书局,1926:64.
[6]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N].时务报:第42册.1898-09-21.
[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48.
[8]孙中山.《民报》发刊词[M].载《民报》第1号.
[9]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
[10]孙中山.孙中山文集:上卷[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325.
[11]申叔.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N].天义报:(6).19071909.
|
|